“太平洋论坛”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系列讲座,本文整理自2020年11月19日太平洋论坛第4期“漫谈跨国史、共有历史与中美关系史”。主讲嘉宾徐国琦为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国际化历史讲席教授,享誉全球的国际史学者。与谈嘉宾是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

主讲人徐国琦教授
主持人马建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香港大学历史系的讲席教授,享誉全球的国际史学者徐国琦老师。徐老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友人,和我们渊源非常深。同学们可能不知道,徐老师第一次来复旦开会,就是参加汪熙教授在1985年11月中旬主办的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可以说是名家云集,一些青年才俊如徐国琦老师、时殷弘老师、牛大勇老师、徐以骅老师、任东来老师等等,都是因为那次会议相聚在复旦。也是在那次会议上,徐老师认识了他的太太,也是我们复旦历史系85届的尤卫群老师,所以和我们的渊源很深。我和徐老师的初次相遇是2004年8月在复旦校园。当时金光耀师安排我来具体负责“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会务工作。那时,徐老师刚从哈佛历史系博士毕业未几年,正在美国卡拉马祖学院任教。尽管是初次见面,徐老师确实对我很信任。会议期间,他说他的新书很快要在剑桥大学出版,也就是《中国与大战》,希望能由我翻译成中文。我当时诚惶诚恐,我觉得我还是硕士生,能够承担这样一个重要的任务吗?大概是2004年冬天的某日上午,我就收到了徐老师从美国寄来的新著China and the Great War,此书的中文版收入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主编的“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之后我就开始翻译这本书,因此跟徐老师结缘。直到今天,我这么多年的学习、成长,一直受惠于徐老师的关照,在徐老师的光芒照耀下成长。
今天徐老师讲的是“漫谈跨国史、共有历史与中美关系史”,我们还特意邀请到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孙国东教授。国东教授的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法学家邓正来先生,邓先生是我们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创院院长。今天,徐老师会把他这些年来做学问乃至人生的感悟,以及对中美共有历史、跨国史研究的展望,与我们分享。
徐国琦(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国际化历史讲席教授):
就像建标教授刚才说的,我跟复旦的确有非常深的缘分。我在国内参加的第一个学术会议,就是1985年在复旦召开和汪熙教授主办的全国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当时,资中筠、李慎之、袁明、金光耀、牛大勇、王建朗等都参加了,老中青学者都在这里。我出国之后在国内参加的第一个学术会议好像也是在复旦。2004年暑假我正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张力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当时要到复旦开会。问我在哪儿,我说我正在上海。张力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金光耀老师,金老师得知后就邀请我参加“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学术会议。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这是我出国之后参加的第一个国内会议。
我的第一本英文书是建标翻译的,第一个中文书评也是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我的另外一本英文书也是复旦历史系的潘星翻译的,所以我和复旦历史系的渊源是很深的。今天这个讲座主要是庆贺复旦历史系建系95周年和纪念汪熙教授诞辰100周年。1985年汪熙教授主办的 “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非常不容易,当时只有复旦、只有汪熙教授才能主办这种会议。因为中美关系在当时非常敏感,我1984年到南开读研究生,立即注意到汪熙教授在1979年写的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那篇文章的观点从今天来看不觉得有什么,但当时我们都是受到丁名楠先生《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影响,把美国都叫做“美帝国主义”,中美关系史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汪熙教授在1979年这篇文章中说,中美关系不仅仅有所谓的对抗,更有友好,所以我们研究中美关系既要看到坏的一面,冲突的一面,更要看到好的一面。当时汪熙教授强调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客观评价,这在我们年轻学者读来是石破天惊的。
我能参加首届中美关系史讨论会,无疑十分荣幸,该会对我们这一代中美关系史学人影响极大。所以这次来到贵校纪念汪熙教授诞辰100周年,非常感慨。从1985年到现在35年了,这35年中国、美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回首当年,的确觉得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今天来,主要是向复旦历史系建系95周年祝贺,也向汪熙先生致敬。

1985年11月14日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合影,第一排右八为汪熙,第三排右十为徐国琦
汪熙先生是安徽休宁人,建标也是安徽人,我也是安徽人。从我个人的角度讲讲国际史或者跨国史,影响我的第一个人是另外一个安徽人唐德刚。在座各位应该知道,唐德刚当年是以整理胡适自传著称的,他的一句名言叫“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唐德刚1981年到安徽师范大学演讲,我当时正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我考大学的时候,英语成绩差不多是零分,但我的数学分数相当好,所以还是考上了。我到安徽师大也不想读历史,所以我说这是开了历史的玩笑,我根本就不想读历史,我一心想做数学家,但是最后数学家当然没做成,阴错阳差,成为一个历史学人。到大学后,我当时天天读《史记》、《汉书》之类的书籍,一心想考中国古代史方面的研究生。1981年左右唐德刚从美国到安徽师大演讲,演讲主题是美国基本概况,提到美国的农业十分发达,让我大吃一惊。我当时以为美国的工业了不起,没想到其农业也如此先进,立即对美国发生浓厚兴趣。从此就把四书五经放在一边,开始学英文,打算研究美国史。
1984年我就投奔到南开大学杨生茂先生门下,杨先生当时开设三个方向,一个是美国外交史,一个是美国黑人史,还有一个是美国史学史,其中外交史是最时髦的,当时他每年只招一个研究生,我十分荣幸成为其美国外交史专业的弟子。1985年汪熙先生主办中美关系史讨论会,杨先生把他的三个弟子都送过来,其中有前几年不幸英年早逝的任东来、现在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孔庆山和我。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国内读研究生时,觉得是赶上最好的时候,我们充满了理想,非常朝气蓬勃。我跟杨生茂先生有个君子协定,他当时承担了《美国外交政策史》的撰写任务,我负责写美国内战到一战的部分,写完之后我就要准备出国留学,杨生茂先生答应了。前几年我在国内出版的一本旁门左道的《边缘人偶记》,里面还收录了当时杨先生给国家教委写的求情信,要求国家教委批准我到美国留学。
1990年12月23号我到达美国,那时的波士顿冰天雪地。当时实际上是前互联网时代,我申请的是跟哈佛大学的Ernest R. May教授读美国历史。我当时不知道入江昭教授已经到哈佛了。到哈佛后,当时系里问我,你愿不愿意改投到入江昭教授门下,因为入江昭教授在哈佛还没有什么学生。
下面我要进入正题,入江昭教授是西方“跨国史”的领军人物,入江昭教授1934年生于日本,他的父亲是入江启四郎,也是著名学者,经典著作是关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所谓的外交关系。过去国内学者都说入江教授是日裔美籍,实际上说错了,他2014年才正式入美国籍,过去长期以来只拿美国绿卡不入籍。
我跟入江教授关系极好,我第一次到他家做客,就问入江教授你家有酒吗?他说有,可能我给他的印象是非常不拘小节的非传统中国人的形象,天不怕,地不怕,比较自信。他对此印象极深。
入江教授1978年四十几岁,就担任美国外交史协会主席。如果大家有兴趣看他美国外交史协会主席的演说,当时他就特别强调“文化”因素。因为过去大家都是强调所谓的“外交史”,都是自上而下从上层研究政治、军事、经济,入江教授就大声疾呼文化的重要性。
到1988年,入江教授成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当年他也才五十几岁,所以入江教授在美国的学术地位是极其崇高。他在美国外交史协会、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演说都是要树立一面旗帜,1978年他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他的著作Culture and Power: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讲述美日关系,特别强调“culture”的重要性。到1988年历史学会的演讲,他就强调历史学的国际化,就是所谓的“国际史”。入江教授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第一本书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就强调多国档案、多国视野的重要性,他用了英文、法文、日文、德文、俄文等资料,展示美国、俄国、英国等国家在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
入江教授作为美国两大学会的会长、“国际史”的旗手与领头人,国内学者对其个人著作比较熟悉了,但注意到他主编著作的重要性,则不多。我认为他后来主编的书中弘扬其学术主张方面影响也同样重要。早在10年前入江教授就开始系统思考和梳理跨国史的路径和门派了,例如他写的这本小书叫Global and Transnational History: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就是一代宗师的大手笔。2012年出版,最近被翻译成了中文。这实际上是入江教授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讲述“国际史”、“跨国史”的前世今生,并对学派的未来做出规划,所以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他主编的另外一本书,就是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可能国内学者也没有特别重视。“dictionary”中文是“词典”的意思,但实际上这里并不是词典,应该是指南。这本书2009年出版,入江教授当时就是要把“国际史”作为一个门类进行规划,所以这本书等于是关于国际史的百科全书。在座各位都是研究生,如果你对某些题目你觉得还不太把握,就可以参考这本书,其中有几百个词条,有长有短。我当时刚刚写完了一本旁门左道的书叫《奥林匹克之梦》,立即奉入江教授之命为本书撰写了关于 “sport”的论文,入江教授编的这本书的开宗明义就是要规划“国际史”,指明“国际史”范畴和路径。如果在座各位对“国际史”或跨国史感兴趣的话,早在十年之前,入江教授个人的书和他编的书,就为大家指明前途了。
相比中国内学术界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6卷本的《哈佛中国史》,我认为大家更应该特别关注入江教授给哈佛大学出版社主编的6卷本的《世界史》。该世界史系列在哈佛和德国同时出版,从国际史的角度,解读全新的世界史。就我所知,这些书还没有翻成中文,个人认为,入江教授主编的这套世界史的影响、跨度、学术地位与含金量实际上比《哈佛中国史》要高得多。其中一卷是Global Interdependence,另一卷是An Emerging Modern World,每一本都是差不多上千页的书,这6卷本世界史无疑是入江教授作为一代宗师,在全方位推广和提高全球世界史研究水平。如果在座各位感兴趣,可以找来读一读,这都是高瞻远瞩的学术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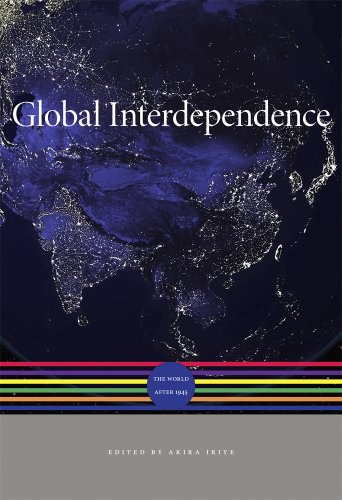
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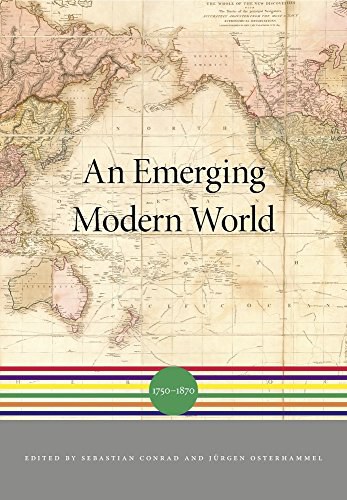
An Emerging Modern World
我个人所取得的任何成果无疑是站在像这入江教授这样巨人的肩膀上的。下面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个人在跨国史方面的一些研究。在入江教授的指导或影响下,我写了三本关于中国的国际史的书,第一本是建标教授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与一战》。2008年,我又写了另外一本左道旁门的书,从体育角度研究中国的国际化,或者说从国际史角度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叫《奥林匹克之梦》。这本书的中文版去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打算尽快出版繁体版,我答应为中文大学的版本增写一章,解读2008年到2050年期间体育与中国的发展及国际化进程。这就是我所谓国际史的第二本书。
我写的第三本国际史专著是《一战中的华工》。研究一战期间来到西线的14万华工。同《奥林匹克之梦》,一样,也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战西线华工80%的人是文盲,他们连汉字都不会,到法国后更不会法语。但他们不少人有法国女朋友。2009年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根据我所写的《文明的交融》一本小书的基本思路,拍了一个6集电视纪录片,叫《华工军团》。里面有好多精彩的故事,从一战华工的角度和经历讲述中国和世界互动的跨国史篇章。
写完国际史和跨国史三部曲后,恰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著名编辑林赛水鼓励我写一本有独创性的中美关系史。我借机思考新的突破。结果就是我的共有历史系列。第一本就是Chinese and American:Shared History。该书英文版于2014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简体字版。繁体字版也在台湾地区问世。2016年底我的共有历史系列的第二部专著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该书的中文本也已问世。我目前已完成该系列的的第三本著作。暂定书名为The Idea of China?。 如一切顺利,哈佛大学出版社应该在2021年左右出版该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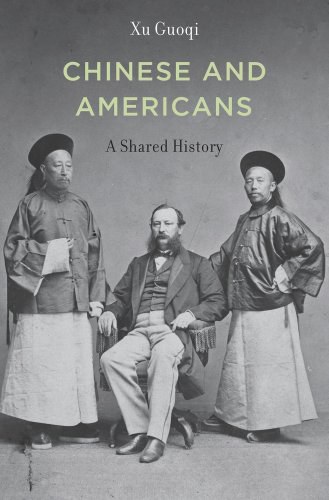
Chinese and American:Shared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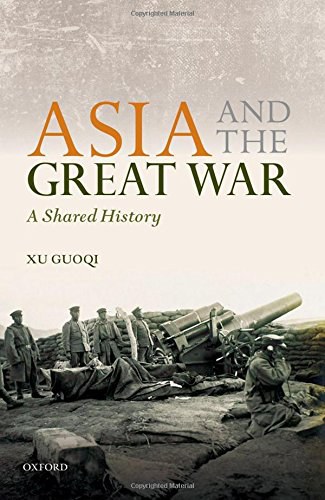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这些书后面都有一个副标题“共有的历史(shared history)”。因为我个人一直认为“跨国史”固然很重要,但是还要往前进,所以我等会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共有的历史”。下面回到中美关系史。就像1979年汪熙教授所说的,看待中美关系不能仅仅从上往下看,必须要从下往上看,就像传教士之类的题目就是如此。历史是客观存在,任何人无法、也无权改变历史。今天我们纪念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如果汪熙先生在天有灵,他应该觉得“共有的历史”符合他1979年的设想,只不过是更大踏步地往前迈了几步。
再次回到1985年在复旦的那次会议。美国学者孔华润也是汪熙教授的朋友,他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每十年都再修订出版一次,在美国影响很大。那次会议上资中筠老师就问,我们何时可以写一个《中国对美国的反应》。中国学者在研究中美关系还有一个瓶颈就是资料缺乏,我们的资料是不对等的,美国的资料很多,但中国的资料却很缺乏。85年的会议上资中筠老师就大声疾呼中国开放档案。
我觉得要走出中美关系史或者学术研究的一个瓶颈,就要回到“共有的历史”,这是我个人的“一亩三分地”。这一概念首先强调“共有(shared)”,一开始我把“shared”翻译为“共享”,2015年我们在澳门开一个小会,北大的牛大勇就说,“共享”好像有点不对,好像是褒义,但是我听你的意思也有贬义在里面。台湾地区的吴翎君教授也是复旦的好朋友,她当年写了好几篇文章,介绍我的学术方法和路径,她认为“共有”更好,我也觉得比我当初的“共享”更好。有些词在英文中很简单,比如“shared”,但翻成中文有时候就很复杂。
“共有的历史”第一个核心就是“共有”,注重中美两国人民和社会所共有或共同经历的梦想、希望、失望、激动和挫折。它侧重文化范畴,这就回到我的老师入江教授的思路,尤其强调个人及非政府机构的作用。 换句话说,“共有的历史”是在我的老师入江教授“跨国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两者是相得益彰,他的基本追求是要强调跨学科、跨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当年汪熙教授所说的也是类似的。所以“共有的历史”或者“跨国史”不仅可以运用到美国史研究,也可以运用到中国史研究,也可以运用在所有的学科,它是一种学术方法。过去我们国内做的“跨国史”研究,绝大部分实际上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地域的概念。现在“丝绸之路”研究如果不从“跨国史”角度,不从“共有的历史”角度研究,实际上是研究不深的。因为“丝绸之路”归根到底是中国人和世界其他人民共同打造的一个历史经历,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通有无的。
基辛格前几年写了一本书《论中国》,其中我记得他就花了很长的篇幅写围棋,因为基辛格认为中国的围棋包含了中国的“战略”,这个战略是跟《孙子兵法》里面的那些战略异曲同工的。所以基辛格认为,要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就一定要懂围棋,所以围棋既是文化又是战略,又是两国关系。过去我们的学者很难从这个角度去看围棋。
我总是开玩笑, 19世纪中国人唯一重要的发明就是麻将。你要研究美国历史尤其美国社区史,研究华人社区和犹太人社区,麻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凡有华人社区或者犹太人社区必有麻将声,所以可以考察麻将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观点不是我的发明,斯坦福大学有一个年轻学者,其博士论文就研究美国历史上的麻将和中国社区、犹太社区。而这些如果从正统的历史史观是关注不到的,只有从这种“跨国史”或者“共有的历史”或者打破民族国家界限,或者从文化角度才能看出来。 哈佛有一个历史学教授伊里兹·马尼拉(Erez Manela),他花了数十年时间研究天花历史。冷战期间美苏两国不共戴天,但美苏科学家联手消灭天花,这就很了不起。如果从传统的外交史角度,就很难关注人类的天敌天花。马尼拉现在也做跨国史,他从这个角度就能写一个很好的关于美苏科学家联手消灭天花这个非常好的题目。
我下面再回到如何从“共有的历史”解读中美关系。在过去,我们一直在纠结,中美关系是合作还是冲突?是强调个人还是政府层面?是文化层面还是政治层面?我的企图是从“共有的历史”角度出发,把这些限制都打破。如果从“共有的历史”解读中美关系,实际上就会读出一种不同的风景线,就像我《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就从6个案例,讲中美两国人民非凡的历史经历。
写书的过程中,也会面临字数限制和题材限制。我当初与Ernest R. May教授讨论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建议我要加两个人,费正清和赛珍珠。 我当时就想,如果要加费正清、赛珍珠,则要加上白修德(Theodore White)。我当时把这三个人的档案都看得差不多,后来还是违背了Ernest R. May教授的意见,不把这些个案收进去。那本书的英文已经400页了,再加上去就很长,一般的英文书如果超过400页,出版成本就会大规模上涨。另外,超过400页的书学生就不爱读了,这也是一个原因。此外,如果把费正清、赛珍珠、白修德放进来,书的体例就改变了,就要收录更多的人进来,例如司徒雷登要不要收录进来?之后的学者如果要找题目,就可以像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样,也踩在我的肩膀上,可以继续写,还有好多题目可以写,特别是关于中美妇女的共有历史,我写《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一个遗憾就是没写妇女。也许有一天我会专门写一本《中国女人与美国女人:一部共有的历史》。
下面我要稍微解读一下,从我的视野来看中美两国有什么是“共有的”历史。中国人和美国人有好多一致的东西,例如我们两国人民过去都很自高自大,中国过去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不愿意同其它国家平等交往。中国一直到1901年才正式有了外交部,过去所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实是临时外交部,没有自己的编制,随时都可以解散。美国也一样,一战之前美国人是不愿意卷进世界事务的,王立新教授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踌躇的霸权》,就是解释美国如何成为世界领袖的曲折历程。美国人认为,自己跟西方国家都不一样。所以中美这两个国家在19世纪前都不愿意参与国际政治事务,都认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当年美国国父们就打破欧洲机制,要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富兰克林当时就建议,或许新美国可以吸收中国的传统儒家文明。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得知中国人不是白人时,一度大吃一惊,他觉得中国人这么聪明,怎么可能不是白人?
所以,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卷进美国历史。波士顿倾茶事件的茶都是从中国来的,当时北美人对英国人对茶叶征税不满。当时十几个殖民地对英国有几个不满:第一是英国人征税,第二是英国人不允许他们自由地接触中国市场,与中国做生意。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独立之后,1784年美国人就派了第一艘船“皇后号”到中国来了,打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限制。所以中国与美国两国之间一开始就互相吸引,美国的独立跟中国是有些关系的。
我们中国一直认为中国是文明古国,美国是新的国家,但如果作为民族国家来说,美国才是最老的。中国1912年成为共和国,等于是一个小兄弟。中华民国建立时,是以法国和美国为师的。美国的共和国比法国还要早,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是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就是在100多年前,1850年代我们中国面临内忧外患,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兵临城下,还有太平天国。美国在同一个时间段完全一样,美国的南北双方不共戴天,那时候实际上是两个美国,一个自由的美国,一个奴隶制的美国。而这时,大清王朝的命运濒临崩溃,因为太平天国对中国儒家文明具有毁灭性打击。洪秀全因为科举考试失败而愤懑不平,之后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跟耶稣是兄弟。就在中国人内忧外患的同时,美国人同时也经历内忧外患。当时最愿意看到美国变成两个美国的是英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内战时英国政府公开支持美国南部。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纠纷是“阿拉巴马号索赔案”,英国人为美国南部制造一艘军舰叫“阿拉巴马”号,这艘军舰给美国北部造成了毁灭性打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内战结束之后,刚刚赢得内战的美国政府就向英国提出“阿拉巴马号索赔案”,美国称如果英国不对美国的损失作出足额赔偿,美国就把加拿大打下来。所以,所谓的中美两国同时期的内忧外患,还有之前提到的自命不凡都有惊人的一致。 我们从传统的中美关系史研究,基本上看不到这一点。
再回到1861年,英法联军开进紫禁城,并火烧圆明园。这就到了我接下来要介绍的主人公展示这段“共有的历史”。中国被打败之后,西方的外交官可以到北京做常驻外交官。谁成为美国的第一任驻北京的公使呢?1861年蒲安臣成为美国第一任驻华公使。今年正好是蒲安臣诞辰200周年,也是他逝世150周年。非常凑巧的1985年11月14日,汪熙教授主办的全国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研讨会”,也正逢蒲安臣诞辰。所以今天我就将蒲安臣作为事例,讲述中美“共有的历史”。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蒲安臣1820年11月14号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成长于美国边疆。因为出生贫寒,所以他的家庭一直往中西部搬迁,例如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在当时都属于边疆州,就有点像我们过去讲的闯关东。他在道德上的高标准和政治上的理想主义,都是他在美国边疆生活的时候培养出来的。从密西根大学毕业,蒲安臣就考到哈佛法学院。在哈佛法学院毕业之后,娶了哈佛大学所在地 Cambridge小城的一个名门望族莉芙茉(Jane Livermore),为他在麻省的政治发展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在1850年代,蒲安臣做了三任美国众议院的议员,众议院是每两年一届,他做了三任所以是6年。1860年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大选的年份,林肯当选总统。当时美国的命运跟此次大选密切相连,但是内战一结束林肯就被暗杀。当时蒲安臣是非常坚定的废奴主义者。
哈佛大学旁边有个美国非常著名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的雕像。他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1856年被一个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差点用拐杖打死。蒲安臣当时作为众议员极其愤怒,他就在国会发表了非常著名的“保卫马萨诸塞”演讲:“我以因这一击严重受伤害的马萨诸塞主权为名,谴责这种行为;我以人道主义为名,谴责这种行为”。
当时在美国,如果两个人之间出现纠纷,有一个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决斗。所以蒲安臣在国会发表演说后,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就向蒲安臣发起挑战,蒲安臣就立即接受。被挑战的人可以决定在什么地点、用什么武器决斗。所以蒲安臣说我接受你的挑战,但是地点是尼亚加拉瀑布。这是在加拿大的旁边,普雷斯顿·布鲁克斯要从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经过敌占区前来,他就觉得很危险。另外,布鲁克斯也知道蒲安臣是非常有名的神枪手,尤其擅长使用来复枪。所以蒲安臣的第二个条件是用来复枪决斗。结果是,布鲁克斯就不敢前来决斗了,这让蒲安臣一夜成为美国的英雄。
但是在总统大选期间,蒲安臣花费太多时间离开自己的选区,为林肯的竞选工作,所以1860年他失去了自己在众议院的议员席位。 作为回报,林肯当选总统之后任命蒲安臣担任奥地利公使。等他到了巴黎,奥地利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因为奥地利政府发现蒲安臣支持科苏特和萨丁人独立。但此时蒲安臣已经到达巴黎,然后他的老朋友国务卿西华德就建议他到中国去,担任中国的公使。所以他阴错阳差到来到中国。
因为当时中美两国是没有利益冲突的,中国人对美国人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蒲安臣到中国之后,他成为所谓的“合作政策”的始作俑者或者鼻祖。因为蒲安臣天生同情弱者,他同情清朝政府,因为清朝政府被英国、俄罗斯、法国欺负。蒲安臣带着他的太太前往中国,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馆面积很小,一年的经费只有区区399美元。蒲安臣就说,美国驻华公使馆是一艘船,但没有水手,是空的。蒲安臣在北京有自己的家,英国驻华公使经常每天吃过早饭就到他家里,一直到晚上再走,因为那个人是一个单身汉。蒲安臣在中国时,他实际上做了好多好事,特别是“文化外交”。因为蒲安臣是律师出身,口才特别好,特别喜欢跟人交流,滔滔不绝,所以中国人喜欢他,总理衙门的文祥、董恂经常给他写诗。因为他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所以他致力于文化外交。
朗费罗《人生颂》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一页,其中就有蒲安臣的影响。朗费罗是美国著名的民族诗人,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馆秘书威妥玛为了练习中文,就将《人生颂》翻译成中文,并将自己翻译的译本交由董恂润色。董恂润色后,蒲安臣说他要回美国一趟,问董恂是否想要给朗费罗写个扇子。按照钱钟书先生的说法,《人生颂》是第一首翻译成中文的美国诗歌,这明显是一个跨国的交流,其中包括了英国人、中国人、美国人。钱锺书《七缀集》就将朗费罗的原作、威妥玛的译作、董恂的润色加以对照。大家如果从哈佛所在地走到朗费罗家大概只需要10分钟,他家现在成为美国的文化遗产,独立战争时华盛顿就住在他家里。他的地下室里面有好多跟中国有关的文物,这面扇子就是镇馆之宝。当年钱锺书先生为了考证这个是谁写的,花了好半天,实际上就是董恂写的。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共有的文化史,是与蒲安臣相关的。
另外,蒲安臣还参与了《万国公法》的翻译。当然,《万国公法》不是蒲安臣翻译的,而是丁韪良翻译的。1860年代大清王朝被洋人给折磨得够呛,他们想要知道国际法是怎么回事。蒲安臣来到中国后,知道丁韪良想要翻译这本书。总理衙门文祥希望蒲安臣能够推荐一本书,蒲安臣就推荐了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非常凑巧的是,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经过蒲安臣的推荐,最后是由清政府出面拨发专款,资助整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并正式进献给当朝皇帝,而《万国公法》在中国的出版影响了日本。我现在有个博士生,我就让他写《万国公法》的国际史,就是写《万国公法》在中国、在日本、在美国的背景和相关历史,日本当时正好是明治维新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这本书的传入影响了日本的历史。而这本书实际上是跟蒲安臣有关系,没有蒲安臣的参与,实这本书能不能被翻译,会不会被出版,董恂会不会给这本书写序都是很难说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例。 过去我们都很少关注,我们都知道《万国公法》是美国人惠顿写的,但这本书的中文翻译的来龙去脉我们不是特别清楚。
另外一个事例,蒲安臣也是中国学者徐继畬所撰的《瀛环志略》一书介绍给美国的人。为表彰徐继畬在中国传播美国之功,通过蒲安臣的安排,美国国务院特赠华盛顿肖像给徐继畬。后来在中美两国民间共同参与之下,在位于美国首都的华盛顿纪念碑上,刻着徐继畬所撰的《华盛顿颂》。这应该说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享历史的另一段佳话。
蒲安臣在北京广结善缘,洋人喜欢他,中国官员也喜欢他。蒲安臣曾帮助中国人解决了与英国的阿思本舰队事件,董恂整整花了5个月时间说服英国人,但英国人根本不理他。我刚才也提到英国公使天天呆在他的家里,最终他接受了蒲安臣的建议,解决了纠纷。按照中国士大夫的习惯,赠诗是友谊和信任的象征。所以蒲安臣要回国的时候,董恂给他写了好多诗,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诗歌原文我没有找到,我专门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去了无数次,在董恂的文集里也没有找到。所以这些诗都是因为从蒲安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的英文手稿再翻译成中文。我请了我陕西师大的朋友王玉华,他是一个诗人,也是历史学家,他出版了两本古体诗词集。我请他根据英文大意翻译了董恂的赠别诗:
春寒犹自别君王,出使依然向远方。
汽笛未鸣肠已断,题诗将罢泪成行。
遥遥黄鹤千万里,片片丹心茉莉芳。
待得明年来归日,真堪置酒赋冯唐。
这是以老朋友的口吻写的,就像“李白乘舟将欲行”。
另外“蒲安臣”这个名字特别好,像英国驻华公使叫卜鲁斯,中国人听着觉得不好,而“安臣”传递出一个积极的形象,因为从字面意义上看,就是“安分的臣子”。接下来讲到蒲安臣与中国卷入美国内战也有关系。刚才我们提到“阿拉巴马号”军舰,蒲安臣就对总理衙门说你们不能让阿拉巴马号来中国,总理衙门很信任他就发布了一项命令,不准该舰接近中国水面。这可能是中国第一次干预美国内政。蒲安臣的朋友马克·吐温特别开心,就在报纸上赞扬中国,说中国是第一个“对我们提供公正友好援助的外国政府”。
1867年蒲安臣已在中国做了7年公使,他想回美国的时候,在北京的洋人非常伤感,如果蒲安臣走了,他们就没处去蹭饭、聊天。中国总理衙门也觉得少了一个老朋友,所以当蒲安臣 1867年11月份向总理衙门准备辞行的时候,文祥给他一个特别的、非常惊人的任命,文祥问他能不能代表中国出使全世界,蒲安臣答应了。蒲安臣穿着全套正式的外交礼服接受清政府的任命,他并没有马上辞去美国公使的职务,甚至没有通知国务卿西华德他的辞职意愿,直到接受中国政府的任命和册封之后才这样做。因为1858年《天津条约》里面有一条规定,10年之内中国人必须要派人出使国外,但当时中国没人去。一是没有合适的人选,二是所谓 “礼仪之争”,中国人到外国去磕不磕头?如果不磕头的话,洋人到中国来为什么向中国皇帝磕头?而中国人觉得蒲安臣已经是久经考验的中国人的老朋友,一会帮中国说话,二是避开礼仪问题。
蒲安臣的妻子莉芙茉也非常高兴。第一,是因为蒲安臣是第一个代表最古老的文明中国出使外国,另一个是因为蒲安臣的工资是很好的。当时使馆一年的经费才不到400美金,蒲安臣作为中国的特使,其薪水据说近3万美元。
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全世界,他的第一站就是美国,与他的老朋友国务卿西华德签订《蒲安臣条约》,梁启超就说这一条约是最平等的条约。1868年美国是一片排华之声,《蒲安臣条约》包括中美两国彼此平等,并涉及到之后的中国留美幼童。因为《蒲安臣条约》第7条规定,中美两国学生可以到对方国家游学,所以说大清王朝或者中国政府第一次官派出国是到美国去的。那时美国的高校跟欧洲的高校相比是小儿科,当时的西方高校最好的在欧洲不在美国,美国的高校实际上20世纪之后才异军突起。如果要研究诺贝尔奖,二战之前美国人占不了多少席位,二战之后美国人才是一马当先的。 但就是因为《蒲安臣条约》,就是因为中国人跟美国人有一种特殊的共有的历史,所以李鸿章、曾国藩才决定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去,归根到底就是《蒲安臣条约》的内容。留美幼童中有一个人叫梁诚,在1908年说服美国总统将庚子赔款多余的部分退还给中国,所以影响了我们另外一个安徽人胡适的精彩人生,此外还有钱学森。所以这就都连起来了,没有蒲安臣就没有留美幼童到美国留学,没有留美幼童当然就没有梁诚,也许也就没有庚子赔款留学生这一系列事情了。
1868年蒲安臣代表中国出使全世界,他最有名的成果就是《蒲安臣条约》。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而《蒲安臣条约》将排华法推迟了好几年,因为美国人说我们是讲究承诺的,《蒲安臣条约》墨迹未干,不能这么做。蒲安臣代表团在美国时是万人空巷,美国总统在白宫高规格接待了蒲安臣使团,美国的国会参众两院联合都搞招待会,这是了不起的。当时接待规则之高,反响之大,今天的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应该很吃惊。当时哈佛法学院教授,还专门写了一首诗,欢迎蒲安臣使团。这个诗当然是是英文,翻成中文大概是这样的:
诞生于新世界的我们,
欢迎远古地球的主宰。
爱默生本来对中国人印象不好,因为蒲安臣他对中国的形象突然大变,他说他对于“与世界上最古老帝国派遣到最年轻共和国的大使,在这个非凡的场合会面”,感到非常喜悦。
如果从公关角度来看,当时大清王朝就任命蒲安臣代表中国进行公关是十分成功。蒲安臣所到之处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滔滔不绝,说我们是代表和平而来,是代表文明而来,我们要寻求合作。
蒲安臣使团中的志刚和孙家谷在收到《蒲安臣条约》后,便拿着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一条条地核对,然后他们得出结论每一个条款都对中国有利。于是他们希望,在出使美国之后,以《蒲安臣条约》作为范本,让英国、法国、俄罗斯也可以比照,但是其他欧洲列强嗤之以鼻,并不理会,唯一的成果就是在美国。当时英国人特别妒忌蒲安臣代表中国,到了欧洲之后,这些老牌列强对蒲安臣条约、对蒲安臣使团实际上是不让步的,所以蒲安臣在英国、法国实际上被冷落了。
在柏林,当时普鲁士要打普法战争,对蒲安臣使团还稍微友好,但是普鲁士当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本来清政府给蒲安臣使团的时间是一年,到1870年初抵达俄罗斯已经超过一年多了,蒲安臣非常焦虑,因为中国对他寄予厚望,他对自己也寄予厚望,所以他到俄国的时候精疲力竭,最后1870年2月份死在俄国,他死的时候是中国的使臣。当清政府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给了他的家人1万元抚恤金,另给6000银两用以把他的尸体从俄国运回美国安葬,并且还追封他为正一品官衔。一品官衔是给皇亲国戚的,此时却给了一个洋人,这可见清政府对他还是很重视的。他的遗体就埋在哈佛校园不远的奥本山公墓(Mount Auburn Cemetery)。蒲安臣这个墓地是中国人出的钱,我找到当年买这块墓地的钱是975美金,这是一笔大钱。应该是来源于清宫的慷慨大方。
前面我就说,梁启超认为《蒲安臣条约》是中国史上最自由平等之条约,可惜我们的中国学者在过去长期忽略了蒲安臣在中美两国人民共有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前面说过,我今天的演讲重在庆祝和纪念。庆祝复旦历史系成立95周年,汪熙教授诞辰100周年。我同时借解读中美共有历史,顺便纪念蒲安臣诞辰200周年和去世150周年。
对话
孙国东(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我是做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的,尽管我个人的研究力图把政治哲学建构与社会—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对历史学一直也感兴趣,但是我对历史研究其实连“票友”都称不上,所以今天我只能谈一些我听完讲座后的学习体会。
我先讲讲我的一个观察,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中国,美国史这个领域似乎一直处在思想解放的前沿,很多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学者都是思想很锐利的学者。徐老师刚才提到的几位学者,像杨生茂先生、汪熙先生、刘绪贻先生、资中筠先生等等都是这样。这让我想起我当年备考高考的时候买的一本学术专著,是黄安年和刘宗绪先生撰写的《世界近现代历史专题30讲》,大家知道黄安年先生也是以研究美国史见长的。我当时看完那本书之后的震撼,与徐老师80年代听到刘绪贻先生对罗斯福新政给予直面评价时的震撼是一样的。因为这本书提到了以实践的观点和生产力的观点来看待世界近现代史,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以及一战二战等等。我高中时是90年代末期,直到那时候,我们学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待西方历史的意识形态观点还是很强劲的。黄安年和刘宗绪先生合写的这本书在当时就起到很好的纠偏作用。为什么美国史领域会成为思想解放的前沿?我想,可能有一个原因是,美国和中国都习惯把对方看作是自己最大的“他者”,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上都是这样。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思想解放工作都是重新认识美国史包括中美关系入手的。
大家都知道,徐老师最有特色的就提出“共有历史”这种观念。我的第一个体会是,这种观念不仅是一种历史观,也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按照我的理解,徐老师其实是在倡导一种“开放的共同体”观念。“开放的共同体观念”是我个人的一个比较直白的说法,如果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社会学家米德 (G.H.Mead)所说出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ever wider community)”观念。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历史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为书写单位,所以我们讲的中国近代史,大部分都是落后挨打的历史、屈辱的历史。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徐老师提到的意识形态性的原因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中国进入现代以来,它的根本使命是要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的一种历史记忆,我们要在现代条件下完成关于中华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现代建构,所以我们就需要激荡起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但是实际上,民族主义不是我们的传统。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讲,我们是天下主义,民族主义只是一个现代的产物。在我看来,徐老师讲的“共有的历史”这种观念,它通过提倡一种“开放的共同体观念”,有可能会打破一种封闭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历史书写方式。
第二个体会涉及对历史本身的理解。我们的历史,特别是西方的社会科学化的历史传入之后,我们总觉得历史是一种 “实证”,所以特别强调史料。但是我们常常忽视了中国历史学本身的传统。在我看来,这种传统其实是把历史当成一种“叙事”(narrative)。叙事和实证的区别在哪儿?对历史“叙事”来说,重要的不是求真的科学精神,而是向善的政治功能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史记》开篇就是《五帝本纪》,但五帝本身在历史上是传说的、不存在的,但是为什么他会写这个?根据我的理解,因为这对于中国塑造一种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有用的,所以它是不是真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就不太重要,中国的国史传统中特别强调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如果把历史当作一种叙事,我们不仅很容易理解中国的“国史”传统,而且可以洞察到历史学研究背后的意识形态预设。这种意识形态预设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西方其实也是存在的。
刚才徐老师提到,在现代早期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形象在美国是非常好的。我记得厦门大学周宁教授专门研究过中国在西方历史中的形象变化。他认为, 1750年大致是西方对中国形象变化的分界点,在此之前,从1250到1450年,从1450到1650年,从1650年到1750年,西方人分别把中国想象成“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和“孔夫子的中国”,那时西方对我们的印象是比较正面的,但在1750年之后急剧下降,就变成了一种叫停滞的、衰败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包括孟德斯鸠、黑格尔在内,我们很容易可以从他们的论述当中看到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评价。同一个中国为什么会急转直下?我们很多人觉得历史好像是完全客观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关于历史的叙事是变化的,会有很多意识形态性的预设。1750年以后,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变化就是这样。这在根本上是因为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现代早期的结束,西方开始进入确立自身现代文化认同的历史阶段,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开始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西方社会都视为文化和政治上的“他者”。在政治哲学中,萨义德有所谓的“东方主义”的说法。什么是“东方主义”?萨义德他们发现,西方人生产的关于东方的知识,就是通过把东方矮化、把东方他者化,从而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确立为东方不如西方的文明等级论。
在我看来,徐老师这种“共有的历史”研究有可能打破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重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这种新的叙事,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种“包容他者的历史叙事”。中国和美国不仅仅是互为他者,我们也有共有的历史。我在为今天的评论做功课时,看到徐老师在采访当中喜欢用的一个词叫“打捞”我们的历史,他提倡通过“打捞”我们的“共有历史”重建我们历史的记忆。我觉得这一点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后,我想向徐老师表达一个小小的疑惑,可能完全是外行的,如果说得不对请见谅。您把“共有的历史”作为一种历史书写的一种新框架。我的理解是,您是将之作为与既有历史主流叙述相对抗的一种新的历史书写方式,这本身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历史书写框架的话,可能还是要面临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怎么容纳近代以来中美之间的冲突。中美之间既然有共有的历史,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发生冲突,这是不是也能从“共有的历史”的角度进行解释。我觉得如果能容纳这一点,我相信这种框架不仅仅是作为对抗既有历史书写方式的学术创新存在,它可以更具有包容性。
徐国琦:我回应一下。我一开始就提到,我觉得原来“共享”这一翻译不好,“共有的历史”就包括正面和负面,不完全是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包括希望和失望,也就是世界上的冲突。比方说,中国人民跟美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冷战理论上是敌人,但实际上冷战期间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共有的历史”就是共同打造的、共同分享的历史过程。
另外,我个人并不认为美国是中国的他者,或者是中国是美国的他者,因为实际上一部中国史或者一部美国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是共同缔造。我举个例子, 2019年是美国环太平洋铁路建成150周年,黄安年先生当年花了很大精力写了《沉默的道钉——建设北美铁路的华工》。实际上美国历史里有好多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斯坦福大学的发起人之所以发财,就是因为中国的铁路华工修建的太平洋铁路,因为太平洋铁路,美利坚合众国在内战之后才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杜克大学的创始人是怎么发财的,大家应该都知道James Duke是给中国人卖香烟,牺牲一代中国烟民的健康发了大财,而杜克大学这段历史我们中国人好像并不熟悉,并不为人所知。所以,不论是斯坦福大学还是杜克大学, 他们欠中国人一个道歉,也欠中国人一个感谢,因为他们的财富是建立在中国人流血牺牲或牺牲健康之上的。
所以,我所说的“共有的历史”并不是完全是正面或负面,是都包括在内的。我为什么不使用“他者”这一概念,在“共有的历史”第三本The Idea of China?中,我提到中国或者美国都是互相参与建构的,也是互相参与创造、参与想象的。中国与美国,又是互相影响、互相牵制,有时互相监督,英文中叫“push and pull”,所以很难说是“他者”或者是“被动”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历史学科的建制出了个问题,把历史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好像历史就是可以从时间上切断的,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划分又将历史从地区上切断。实际上,历史是人类所共有的,也是跨国的。为什么过去我们的历史学者研究一战比较薄弱,因为一战既不是中国史,也不是世界史。研究“丝绸之路”,也要从跨国史的角度,因为这不只是中国古代史或者是世界古代史,它涉及到多重视野、多重档案。我有时开玩笑,我要是回国工作,可能是找不到岗的,因为我的研究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甚至是不伦不类。我既不是中国史也不是世界史,既不是古代史也不是现代史,我做的题目是经常是游离的,比方我一会儿做一战,一会儿做体育,一会儿做中美关系。最近我写的这本书纵横3000年,从春秋战国一直写到现在,梳理所谓的Idea of China是怎么来的。其中既有中国自身的因素,也有外国的重要影响和参与。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